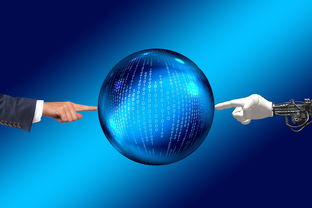编者按
《域外视野》栏目主要推介域外作者撰写的有关体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包括域外学者的研究前沿综述、重要研究成果介绍与评述及一些学术访谈等,旨在为国内的作者提供一个管窥域外相关前沿研究进展的窗口。本期栏目中首次推出学术对话录——《作为技艺的体育社会学:我的学思历程——约瑟夫·马奎尔教授学术访谈录》,以问答形式完整还原了采访对话实录,对话中传递了前国际体育社会学主席马奎尔教授的体育社会学研究历程。在此,诚邀各位专家学者能为我刊提供更多域外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凯文·杨,教授,研究方向:体育社会学。
通信作者简介
洪建平,北京体育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体育媒体和社会。

摘要
约瑟夫·马奎尔教授是体育学科全球排名第一的拉夫堡大学荣休教授,也是过去50年欧洲和北美体育社会学最重要的体育社会学者。研究领域为体育、文化和社会,包括体育暴力、运动损伤、运动和身体/情感、体育和媒体等,当前关注体育和社会理论、体育和全球化。以学术访谈录的形式,从马奎尔教授的个人视角反思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以及体育社会学的技艺,或可对国内体育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实践有所启迪。访谈涉及马奎尔教授个人的学术师承、研究轨迹,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和角色,体育社会学研究方法、体育社会学家的使命、体育社会学者与体育参与的关系、体育社会学教学实践的反思,体育社会学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语境下的历史脉络、发展现状、问题和未来展望等。
关键词:国际体育社会学;教学与科研;社会实践;马奎尔
约瑟夫·马奎尔(Joseph Maguire)是英国拉夫堡大学体育、运动和健康学院荣休教授,曾在莱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Leicester)获得体育社会学博士,担任过两届(2002-04和2004-08)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y of Sport Association)主席和国际运动科学和体育委员会(International Council for Sports Science and Physical Education)执委。2010获北美体育社会学学会(North American Society for the Sociology of Sport,NASSS)杰出贡献奖,2011当选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荣誉会员。研究领域为体育、文化和社会,包括体育暴力、运动损伤、运动和身体/情感、体育和媒体等,当前关注体育和社会理论、体育和全球化(文明内部关系,奥运会和大型体育赛事,移民、媒体和民族国家认同,体育和发展)。
马奎尔教授已出版体育社会学著作近20本,发表学术论文100多篇。其中早期的两本著作《运动世界的社会学》(Sport Worlds: A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2002)和《理论阐释:体育与社会》(Theory, Sport & Society,2002)分别被翻译成中文繁体和简体出版。最近在版的两本著作是《反思过程社会学和体育:一往无前》(Reflections on Process Sociology and Sport: Walking the Line)和《体育社会科学手册》(Handbook for the Social Sciences of Sport)。根据仇军、田恩庆在《欧美体育社会学研究图景》(2016)中的引文统计,在欧洲和北美体育社会学共同体中都被高度认可的三位最重要的被引作者,其中有两位是来自社会学领域的布尔迪厄和福柯,来自体育社会学领域的唯有马奎尔一人。从马奎尔教授的个人视角反思国际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以及体育社会学的技艺,或可对国内体育社会学教学和研究实践有所启迪。

理论诠释:体育与社会
1 关于学术师承和研究轨迹
问:
埃里克·邓宁(Eric Dunning)教授去年的离世是国际体育社会学界的重大损失,作为西方体育社会学的学科奠基人之一,他与导师罗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合著的经典体育社会学著作《寻求刺激:文明进程中的体育与休闲》以及领衔完成的关于球场观众暴力问题的系列研究著作以“莱斯特学派(the Leicester School)”而闻名,在体育社会学界被认为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我们知道他指导了您在莱斯特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说说他对您的影响吧。
马奎尔:我与邓宁教授的第一次相遇大概是在1975或1976年,我记得是在伦敦的大学图书馆。这里我说的“相遇”不是现实中的见面,而是通过他编辑的文集《体育社会学读本》。当时这本著作被我的研究生课程导师之一鲍勃·皮尔顿(Bob Pearton)列入课程阅读材料模块,他后来和邓宁、我在1993年合编了《运动过程》一书。事后证明,阅读这本论文集的时机和地点对我日后接受型构/过程社会学研究(figurational/process sociologicalstudies)具有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重要意义。我下面会详细解释一下。
在英国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老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和马克斯·韦伯开创的诠释社会学(Interpretive Sociology)资源被重新发掘出来。这个趋势在社会史研究、教育社会学的新发展以及越轨和犯罪学研究的批评转向中都得到体现。我在历史和教育学方面的老师们那里受益良多,其中也包括鲍勃·皮尔顿教授的体育社会学课程。正因为他们,我才开始接触一些经典社会理论著作,包括布罗姆(Brohm)、霍克(Hoch)、里格尔(Rigauer)和文奈(Vinnai)等当代理论家的著作。对当时的我来说,这些著作都很有启发。当然,这些著作不乏争议,但著作中那些深具洞察的意识本身也在发展过程之中(consciousness-raising)。
不是所有的同学都像我这样受这种“激进”的思想所影响。这可能跟个人经历有关,包括中学和大学所受的教育,也与我的“局外人”身份相吻合,我是一名爱尔兰天主教徒,成长环境跟反叛的歌曲和抵抗的故事联系在一起,爱尔兰人历史上与英格兰人有宗教冲突。当时学术界对性别或种族问题的直接关注还很少,当然后来我重新阅读文奈发现他的作品实际上对男性气概(masculinity)研究有所贡献。总的来说,关于抵抗的研究主题主要还是基于阶级和民族主义的。一些自由女权主义者的作品,以及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1982)和爱德华兹(Edwards,1985)等学者对种族和体育的解读后来才陆续出现。重要的是,因为所学的课程不是模块化的,所以我们有大量的时间自由阅读。书单上要读的书图书馆都有。体育哲学与教育哲学课程有相通的地方,萨特(Jean-Paul Sartre)、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齐克果(Søren Kierkegarrd)和阿尔弗雷德•舒尔茨(Alfred Schultz)的书都要读,之后回想起来,我才意识到这些阅读最终影响了我如何写我所谓的“寻求激动人心的意义(quest for exciting significance)”。当然,这就说得有点远了。
暴力和体育问题是体育社会学课程的重要内容。事实上,这也是鲍勃·皮尔顿在埃里克·邓宁指导下正在研究的领域。埃里克·邓宁也偶尔在伦敦大学教育学院(University of London 's Institute of Education)授课。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有了的第一次见面。我记得那是1978年,具体的话题我记不太清,好像是英格兰足球社会历史方面。课程导师和未来的论文导师都是朋友,作为当时英国学术圈非正式的交往方式也是埃里克·邓宁的学术惯习,我被邀请跟他们一起喝啤酒,听他们讨论体育运动。
我对体育的最早研究可以追溯到一篇本科课程论文,主要是从符号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t)和现象学的视角(phenomenological perspective)探讨成为/作为一名体育教师的过程!当时功能主义定量研究已经风光不再,我说的是20世纪60年代流行的那种诸如寻找体育参与和学术成就之间因果关系的研究,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现在这些玩意儿又重新流行了。当时在我的视野范围还没有一本型构社会学的著作,最接近的就是伯恩斯坦以及他对阶级、符码和控制的研究。更广泛地说,当时我的知识背景还局限于教育社会学课程阅读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符号互动论/现象学对体育的研究文献阅读,我的学术可能性就停留在这了。但是接下来改变发生了。
因为申请到了英国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的博士研究生资助基金,我从伦敦来到 了莱斯特,在这之前我曾想过申请一个美国大学的硕士学位研究生助学金。莱斯特大学拥有战后英国实力最强的社会学系。埃里克·邓宁和帕特里克·墨菲(当时是社会学系的高级讲师)已经从SSR 获得基金资助研究足球流氓(football hooligan)暴力的社会根源。埃里克·邓宁指导的研究生资助方向跟我的学业和社会背景正好契合。我的论文最后研究了从维多利亚晚期到20世纪70年代足球流氓现象作为一个社会问题的长期存在,这应该是第一篇关于足球流氓的博士论文。
对我来说比获得博士学位更重要,对我学术生涯产生更长久影响的是埃里克·邓宁的指导风格和那些更本质的东西。作为导师他重视社会学技艺(sociological craft)的传承和学术惯习(academic habitus)的培养。在一门教授写作技巧和以过程社会学(process sociological) 的方式进行学术写作的研究生课上,他让学生避免使用把过程简化为静态变量或陈述的语言(using language that reduced processes to static variables or states),避免优先考虑某个单独变量或没有可靠证据支撑的先验假设的思维/写作风格(thinking/writing style that gave primacy to a single variable, a priori, and thus,in advance of where the evidence led)。社会科学研究中长久以来一直有介入(involvement)还是超脱(detachment)的争论,埃里克·邓宁 显然是一位介入的学者,或者说一直致力于韦伯意义上作为一种志业(vocation)的社会学,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影响着我一直践行这条道路。
这种智识惯习(intellectual habitus)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批判倾向,它包容好奇心,跨越时间、空间、地点建立联系以看到更大的社会图景,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大历史”。虽然这在当时甚至现在仍然是一项进行中的工作,但对于身处其中的研究者来说却是一种享受,研究社会现象进而探讨它的意义本身就令人兴奋且乐趣无穷。我现在把这看作是一种游戏形式——种类似于赫伊津哈(Huizinga)的游戏人(homo ludens)意义上的社会学游戏 (sociologica ludens)。
问:
我们都知道正是邓宁教授与他的导师埃利亚斯一道打破了英国社会学界存在的对 于将体育纳入社会学研究范围内的蔑视与摒弃这一僵局。邓宁在埃利亚斯指导下的毕业论文聚焦于足球是如何从过去粗野狂放的民间游戏发展到如今以具备明文条令的正式组织为特点的现代运动,其中,制定详尽书面规则的目的之一,就是来约束、管控并逐步降低内核于比赛间的且被社会大众普遍允许的暴力行为,这无疑是文明进程的体现。邓宁教授极大拓展了埃利亚斯型构理论(过程社会学)的应用范围,奠定了“莱斯特学派”在体育社会学 领域的核心地位。能不能谈谈您的研究轨迹与埃利亚斯在莱斯特大学开创的型构社会学传统的关系。
马奎尔:作为莱斯特学派(Leicester School)的一员,尤其是在这个学术脉络下攻读的博士学位,一般人们会认为必然要跟型构/过程社会学发生关联,但了解到埃里克·邓宁提供的学术研究自由度可能会让这些人吃惊。“去做你想做的吧”(Go where you’re thinking takes you)是他的口头禅。因此,虽然邓宁对我的社会学技艺和学术惯习的培养至关重要,出于兴趣我也广泛阅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史、批判犯罪学和新兴的文化研究。当然,在我的论文中,所有这些东西都被我整合在一起,以理解作为社会问题的足球流氓现象。当然,此后随着其它学者如格鲁尼奥(Gruneau)、哈格里夫斯(Hargreaves)、沃内尔(Whannel) 和惠特森(Whitson)等的著作陆续出版,体育社会学研究的领域也不断拓宽和深化。我没有去牛津大学做犯罪学博士后,而是接受了一个体育社会学教职,开启了我的人生后半场。
从我的博士论文的文献阅读构成来看,我不认为哪一派可以霸权式地宣称自己这一派绝对重要(critical),也不同意某些人所说的各种研究取向(strands)的综合会不兼容。对我来说,这些不同的研究视角相互重叠,综合各种研究方法,是我们理解体育、文化和社会的必要途径。我现在仍然是这种观点。事实上,在我的博士论文完成之后所做的身体和全球化研究中,我就综合使用了各种研究取向的方法,只要我认为它充分且必要。而型构/过程社会学方法成为我整合其他观念、思维和方法取向的指导原则(lodestar)。
对身体的研究扩展了我对暴力的思考,以及进而对情感、身体、损伤(pain and injuries)的研究。这时候不管是有意识还是没有意识,某种意义上我是在重新思考埃利亚斯和邓宁1986年出版的《寻求刺激》(quest for excitement)的核心观点。从文献阅读和我自己的经验研究中,我得出了这样一个观念:理解体育运动的攸关所在是“寻求令人兴奋的意义” (quest for exciting significance)。事后来看,我真希望我沿着这个研究脉络一直继续,当然我指导的那些博士研究生已经在这方面推进了不少。遗憾的是,我自己没有尽可能充分地探索日常经验、认同冲突、体育生活的象征性和存在维度(symbolic,existential dimensions of sporting lives)。在随后的好几年里,我的好朋友、杰出的同事艾伦·克莱恩(Alan Klein,1991)经常对我说,我本来应该跟他一道在人类学领域做更多的工作。
我的学术生涯早期关于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的研究跟 1980 年代英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争论有关,也是认同政治(identity politics)问题的反映,它涉及到我自己的身份、个人经历和家族史,只要生活在英国的爱尔兰人都明白怎么回事。因此, 在从美国化问题转向更广泛的全球化问题讨论的过程中,我的研究涉及国家重构(reconfiguration of the state)的问题、一直存在的国家和民族主义的重要性、与全球流动相关的问题、跨国公司的角色以及运动医学产业联合体(sports medical industrial complex)的出现。我目前的研究转了一圈,又回到了认同、民族和民族主义问题。
回顾过去,身体和全球化的这两个主题好像是一个大项目的两部分,实际上不是。我的研究兴趣和关心的问题只不过是我所处的社会潮流和学术动向的折射。当然在这个过程中,我个人为体育社会学的发展也做了一些努力。在全球层面,我担任过国际体育社会学学会(International Sociology of Sport Association,ISSA)主席、与母学科社会学研究团体接触以 使体育研究更广泛地合法化。在国内,我试图将体育社会学定位于体育和运动科学(sport and exercise sciences)之中,为了确保体育社会学得以发展和繁荣的权力资源和它的学科地位, 我们不得不与自然科学打交道,这不仅是在拉夫堡大学,在整个英国也是这样。传统的体育 社会学研究和教学方式在过去三十年中可能行得通,但现在情况不那么乐观。
2 关于现代社会中的体育
问:
从一个社会学家的角度,您怎么看待体育在社会中的地位?
马奎尔:与艺术相比,体育似乎看起来不那么重要。这是价值判断。在艺术研究中,社会学家一般不会试图去作审美判断。而且,正如 Georg Simmel曾经敏锐指出的那样,看似平凡的事物可能具有重要意义。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的角度来看,体育是非常重要 的。事实上,正是运动的日常平凡性使它如此重要,与社会运作缠绕的那么深。我将以英雄 和体育比赛中冠军的社会角色为例解释一下体育和社会的关系。
荷马的《伊利亚特》(The Iliad)和《奥德赛》(Odyssey)是西方文学中现存最古老的两部作品。他们创造了英雄事迹和像赫克托和阿喀琉斯这样的战士形象。这些英雄是他们城邦的冠军,他们的品德被荷马以一种传世的方式记录下来。今天再读这些传奇,除了记录下的英雄主义的生活和身体经验,它们还给我们留下了什么?这些神话对我们理解今天的体育有什么启发?成为比赛冠军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他们对我们意义如此重大?简单地说,冠军是在所有参赛者或竞争者中的第一名,在这一点上,这个词指的是个人或团队赢得比赛的能力。然而,在英语中,“冠军”的词源表明了另一种不同的含义,它提供了一个理解的线索, 为什么冠军对我们来说比他们赢得比赛的能力更重要,以及为什么我们要把这样的意义附加到他们身上。在英语中,“冠军”一词最初用于中世纪的骑士比武中,指的是某人的拥护者 (the person who would act as a champion of others)或者保卫、支持或维护一项事业 (champion a cause)的人。
从这个意义上说,运动员不仅仅是他们运动项目上的冠军,也是他们当地社区和国家的拥护者,有时甚至是整个人类的拥护者。已故的美国拳击运动员穆罕默德·阿里(Muhammad Ali)就是出类拔萃的典范。冠军要有特殊的天赋和独特的个人魅力(charisma):他们上演奇迹,使看似不可能的事成为现实,就像荷马笔下的英雄。冠军运动员是我们现代的英雄,我们文化价值观的象征再现(symbolic representations),也是我们希望成为的人。冠军是拥有天才的人,但作为英雄,他们是在向我们也向其他国家的人们讲述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whose lives tell stories about us)。
人们欣赏卓越,并且也渴望追求卓越,即便无法做到也愿意分享卓越。冠军可以让我们窥见人类的潜能:他们代表我们感受什么是终极体验(make us vicariously fulfilled human beings)。他们是我们现代的英雄,因为体育已经成为集体自我展现(self-revelation)的公共场所。不妨说,现代体育是某种形式的宗教替代品(surrogate religion)或者大众戏剧,人们聚在这里,集体意识到我们是谁。在体育场上,我们把冠军视为英雄,暂时抛下日常生活的世俗,去体验“神圣”时刻令人兴奋的意义(experience the ‘sacred’ moments of exciting significance)。在这个意义上说,社会需要作为英雄的冠军,他/她们发挥着为自己、当地社区和国家实现体育成功的显功能。但他/她们也扮演着一个更为隐藏的角色:他/她们必须体现最被社会看重的那些价值。作为理想化的造物(creations),他/她们为人们提供灵感、 动力、方向和生活的意义。作为英雄,冠军具有整合社会的功能,以一种共同的目标感和价 值观把人们紧密地团结起来。现代体育就是这么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的先驱们将体育运动 与强身派基督教(Muscular Christianity)联系起来:无私、自制、公平、绅士风度和道德高尚。这本身就是对传统骑士精神的补充:荣誉、体面、勇气和忠诚。而这些品质恰恰是退 役多年的英国足球运动员博比·查尔顿(Bobby Charlton)爵士以及最近几十年冠军们所具备的人格特征。
问:
在文化领域确实没有比体育更需要英雄的了。而且体育与娱乐工业还不一样。娱乐工业的明星未必是英雄,即使他们能够在虚构角色中发挥作用。其他如军事和政治等公共领域的特点是为英雄主义结构性条件的出现提供传导功能,而且不会分享英雄叙事日常具有的贪婪胃口。以至于当代体育似乎给大家造成了一种错觉,即英雄都是出自职业体育运动。但在大众媒体中我们今天也经常看到体育英雄坠落的故事。
马奎尔:确实在博比·查尔顿身上体现了高贵的品质,但冠军们并不是都像他那样,英雄的光环因此受到了威胁。问题一般与真实性(authenticity)和诚实正直(integrity)有关。冠军的地位取决于比赛的真实性。如果比赛被腐败、作弊、兴奋剂或赌博丑闻玷污,那么英雄在我们心中的形象就会打折扣。比赛不再是共同追求卓越或者集体自我展现的社交舞台。当体育变得太虚假、被操纵或者毫无悬念,它便缺失了真实性。竞技运动(Elite sport)产生冠军,但并非所有冠军都是英雄。职业摔跤也会产生冠军,但却不被人们重视,他们不会成为我们的英雄。此外,如果冠军代表着一个不被民众支持的体制,对他们的尊重就会缺失。换言之,运动员可以成为抵制的符号,透过他们可以窥见不同的体育制度。
如前所述,作为英雄的冠军也体现着一个社会最看重的价值。但是,冠军的道德神化 (integrity)也可能在几个方面受到削弱。冠军可能是有缺陷的天才——要么是因为骄傲自大,觉得自己在比赛准备和表现上不需要投入那么高的水平和强度,要么是因为他们的私生活违背了他们作为英雄的身份。说到这里马上就会想到前英格兰国家队队员保罗·加斯科因 (Paul Gascoigne)的例子。因为天赋出众少年成名,让加斯科因承受过多来自媒体的压力。2002 年退役后,因为酗酒甚至面临无家可归的窘境被媒体关注。他作为运动员的理想形象也被打破了。此外,我们的冠军是名人却不是英雄,他们有名但缺乏英雄气质(famous but not heroic)。大卫·贝克汉姆(David Beckham)也许可以视为这种类型。如果事实如此,那这样的名声是短暂的,他们经不起时间的检验。为了更好地理解冠军对于我们的意义,以及 他们的影响,我们不得不思考体育在社会中扮演的角色。
体育既是一个独立的世界,也是对日常生活的暂时搁置(suspension)。然而,它更是其所处的的社会的高度象征,并嵌入更广阔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潮流之中。在体育的场景里,我们既可以体验在日常生活中很少有的兴奋,也像是进行了一场与其他参与者和观众 的象征性对话,从中可以发现我们自己和他人(身份/认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遮掩的恰恰是在运动场里暴露出来的。体育是现代的道德剧,展现人类作为个体、群体以及相互之间关系的底层真相(fundamental truths)。体育在情感上打动我们,在社交上也很重要,而体育之所以能够发挥这些社会功能与冠军的作用息息相关。
体育的主要特征之一就是引起令人愉快的兴奋感(excitement)。在日趋规则支配和风险规避的社会,人们似乎产生了一种新的需要——体验各种自发的、初级的(elementary)、肤浅(unreflective)但令人愉悦的刺激。在体育比赛中,不论是参赛者还是观众,人们都在寻求一种压抑后的情绪释放(controlled decontrolling of emotions)。这样,情绪以一种激发或模仿现实生活情景中产生兴奋的方式自由释放。因此,体育是模拟活动,它提供一种虚拟 的独特场景(‘make-believe’ separate setting)让情绪更容易释放。这种兴奋卷入了想象或可控的“真实”危险、模拟的恐惧和/或愉悦、悲伤和/或快乐,但这一切都是由人为制造的紧张所引起的。这种压抑后的兴奋释放使得各种情绪在这一虚拟的情景中被唤起,这些情绪其实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翻版。我们的冠军之所以被认同不仅仅是是因为他们的技术造诣,而且也因为他们和我们共同经历的情绪,比赛的精彩、紧张或刺激。
网球比赛中的抢七局、足球比赛中的点球决胜和高尔夫加时赛中的突然死亡等都会导致一系列的情绪变化,这些情绪变化如此强烈以至于在比赛结束时,我们都感觉精疲力竭。而且,这不同于精心策划的戏剧或电影,我们知道所目睹的体育比赛是真实存在的,比赛的结果也不是事先确定的。冠军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也成就了我们的梦想,但更多的时候要经受失败的悲剧。在温布尔登中心球场的入口处可以看到墙上的一块匾牌,上面刻有鲁德亚德·吉普林(Rudyard Kipling)的诗“如果”里的一段。诗句的意思是:当你遇到胜利和失败的时候,必须用同样的心态来看待它们(If you can meet with Triumph and Disaster,And treat those two impostors just the same)。在温布尔顿网球决赛中面对胜利与失败时,费德勒可以 说是体现出了这样的情操。
只有当体育运动与深层次的文化意义和个人意义相联系时,它们对体育迷来说才变得重要。因此,重大体育赛事成为给体育迷提供实现集体参与和认同机会的神话奇观,也是颂扬和强化共享同的文化意义(celebrating and reinforcing shared cultural meanings)的一种方式。正因为体育是一个将日常生活暂时搁置的独立世界,它们才能够颂扬由冠军们所表达和体现出来的共享文化意义。与体育比赛联系在一起的国歌、会徽和国旗凸显了冠军代表的是一个国家。1966 年夺得世界杯冠军的英格兰足球队就被赋予了集体英雄主义的精神。他们的成功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至今仍然让英格兰球迷为之感动。当时的英格兰足球队队长鲍比·摩尔(Bobby Moore)虽因癌症英年早逝,但他的标志性形象仍然铭刻在人们的心中。这给我们一个启示:体育的象征意义以及冠军所扮演的角色,甚至比单纯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要深刻。鲍比·摩尔成为比获胜更有意义的象征符号。
如果可以把社会生活看作是一场比赛,通过这场比赛,身份/认同得以形成,并得到检验和发展,那么体育或许是社会生活的理想形式。体育比赛的的游戏规则(如高尔夫球礼仪 )要求公平竞争和对能力的真实检验。在真实公正的比赛中获得“真正的”冠军,就是对这一点最好的体现。正是在这种情境下,才有可能建立起比现实社会生活中更加一致和可靠的身份/认同。我们强调比赛的真实性和公正性(integrity),也就是严格的正式规则以及公 平的实施,因为我们希望人们之间的任何价值差异都建立在美德(merit)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阶级、种族、性别或宗教干预和操纵着社会生活中的游戏及其结果。因此,不论胜利者还是失败者都成为亵渎的假象。但是,在运动场上,体育比赛的结果是神圣的,它们真实而可信,这也是为什么冠军们总想击败势均力敌的对手,因为那才是真正的考验。事先就知道你将会打败比你差的对手是不会赢得荣誉和尊重的。1970 年世界杯期间英格兰对巴西的比赛鲍比·摩尔和贝利(被广泛认为是有史以来最好的男子足球运动员)在球场上的握手象征着这样的荣誉和尊重。而阿根廷球员马拉多纳的“上帝之手”不会赢得这样的荣誉和尊敬,虽然他也是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这粒进球得分也许体现了他的爱国主义精神,但却削弱了他作为更宽泛意义上的英雄声望。
因此,体育是一种象征性的对话:对话如何进行有着严格的规定性。体育涉及对我们是谁和我们想成为谁的戏剧性表达(dramatic representation of who we are and who we would like to be)。体育场就像一个剧场,在这里我们体会一系列令人愉悦的情感和令人激动的意 义:在比赛中,兴奋随着结果的变化而变得不确定,但它的意义来自于我们在情感、道德和社交上的投人。冠军们作为现代的神话英雄表达了这个社会所崇敬的价值,也体现了构成体育参与基础的体育道德。为了展示他们勇敢无畏和正直的品格,他们不得不承担风险。这就是我们记住他们的原因,就像我们记得赫克托和阿喀琉斯一样。这也是为什么体育很重要的原因所在。
3 体育社会学研究及其实践
问:
参与和介入是社会学者理解他们试图研究的世界的必要技巧之一。与此同时,作为参与者的社会学者又必须能够与研究对象保持一定距离,从而成为观察者和解释者。就您个人的经验看,研究体育社会学需要喜欢或日常参与体育吗?
马奎尔:在我的职业生涯中,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评论,“从你写的东西看,你一定不喜欢或不怎么参与体育活动”。但是,问题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也可以反问一句:体育社会学者需要喜欢体育吗?毕竟,在研究犯罪比如谋杀时,犯罪学研究专家不需要喜欢杀人犯,也不必杀过人犯过罪。从理解(verstehen)的角度而言,这不是说你不需要让自己参与并沉浸其中,尽可能使你的观察就像亲历者自己所见一样(还是需要的)。
尽管如此,我年轻时喜欢的运动并不是我现在喜欢的。我的观察点也不一样了。我知道的更多,我作为参与者的角色现在更复杂——普通一员,观赏者,教练,家长,观察者,活动家和社会学家:想看一场精彩的比赛,体验一场爱尔兰战胜英格兰的英式橄榄球比赛激动 人心的意义,在孩子参加体育活动保护他/她,关注全球体育权力精英和运动医学产业联合体中的不平等现象并对其进行批判性分析,这些角色之间并不矛盾。
然而,全球体育的核心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被腐蚀了。大学校长们对体育系很是敬畏,前运动员热衷于攫取权力而纵容其运动项目中滥用毒品和腐败,运动医学产业联合体的触角伸向了体育界的各个层面。在大学层面上,这损害了大学的使命,有助于其重塑世界一流大学的公司品牌,却使学院派批判性思考者边缘化。我们不必喜欢体育,对我们在运动世界中看到的趋势也是如此;我们的任务是捕捉事物的本来面目。对体育社会学家来说,这项任务在近些年来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问:
从方法论上来说,您认为社会中的体育应该如何去研究?
马奎尔:如何研究体育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与研究的性质和范围有关,是作为主流社会学学科的一部分,还是体育和运动科学的一部分。寻求功能/作用、影响和快速解决问题的方案容易让你相信体育是一种社会粘合剂、一种社会资本和/或灵丹妙药(panacea)。我们有必要重新思考和定位这个争议问题和它的重要性。体育社会学家应该提(make)属于他们自己的“问题”,而不是被动“接受”(take)体育界的主导者(advocates)给他们界 定的问题。实际上,我们需要考虑什么是社会问题,包括它的客观条件和主观定义。显然, 那些掌握权力的人和那些主导体育管理和商业课程的人不愿意看到体育社会学家们将当今 体育界看作是运动医学产业联合体的另一面。体育作为社会问题灵丹妙药的说法缺乏证据基础,甚至,这个问题本身就是错的。事实上,体育也可能导致、加剧和制造新的社会问题。基于功能和影响的灵丹妙药观是意识形态卷入和魔术般的神话思维的表现。对此我们需要更客观和超脱(detachment)的态度。
置身于社会学,你取向哪种社会学解释也会定位你的研究。我的方法借鉴了型构/过程社会学,但也涉及社会学的其他领域和方法。在研究“作为集体活动的艺术”时,贝克尔(Becker)阐述了特定的艺术表达如何置身于由供应商、演出者、经销商、代理商、经理、 评论家和消费者组成的网络之中。在这个网络中有一系列习俗、禁忌、权力斗争和商品链,每一个对网络运作和艺术生产都必不可少。体育表演也一样。艺术界由那些对艺术生产活动不可或缺的人组成。贝克尔在研究这些人是如何互动的时候,提到了“活动的协调”,“日常实践中体现的合规性理解(conventional understandings embodied in common practise)” 和“参与者之间建立的合作关系网络”。
我对构成和形塑社会、体育和生活的一系列相互依存性的看法与贝克尔的网络观有着密切的联系。正是沿着贝克尔和诺伯特·埃利亚斯的研究路径,我将“运动世界”作为相互依 存的人群的网络或型构(figurations)来研究。理解构成运动世界的网络基于以下四个关键的主要观点:(1)人类是相互依存的;他们的生活是由他们互动形成的社会型构演变而来的,其发展受到这些型构的显著影响;(2)这些型构处于不断变化之中,有些变化快速而短暂,有些缓慢但可能更持久;(3)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发生的长期型构过程,大部分都是意外和无法预见的,过去是将来也是;(4)人类知识的发展是在人类社会型构中发生的,并形成人类整体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这些基本观点为理解体育界提供了一些大致的方向,其中贝克尔对艺术界的洞察也有助于对体育现象的分析。在贝克尔看来,艺术界有五个不同的特征,如前所述,第一个特征是网络(networks)在艺术生产中的作用。第二,围绕艺术界的界限是可渗透的,这意味着不 参照其他界别,很难辨别什么是艺术什么不是艺术。而且,所谓艺术的生产依赖于社会其他界别。第三,当艺术界中人试图将他们的世界与其他界别区分开时,他们也与其他界别的人 们有着“亲密而广泛的关系”。第四,艺术界是由传统维系的,但也不乏创新和挑战。最后,艺术界有一定程度的不受其他群体和社会世界干扰的相对自主性。贝克尔似乎过于强调艺术界的合作维度(或者说淡化构成这些世界的权力斗争),实际上他在质疑艺术表达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由”和自主的。
从这个角度考虑,体育可以作为一种集体行动(collective action)来研究,它涉及到在特定网络中相互连接的各种各样的人,正是他们创造了特定形式的体育产品或表演。前面提到的“合规式理解”,可以用来观照体育亚文化和管理体育实践。此外有必要从体育界所处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来批判性地审视体育界“相对自治”的程度。建立将体育界与其他社会世界联系起来的网络既要关注合作的过程,也要关注对抗的过程。就像与盟国和敌人之间的关 系,合作和对抗是塑造体育界的网络的特征。作为研究体育的社会学家,就像研究艺术、宗 教、医疗和劳动的同行一样,我们都是在研究人们如何处理相互依存的问题。
问:
您对体育社会学的未来发展有什么建言,或者说对年轻一代的体育社会学者您有 什么想对他们说的?
马奎尔:为了使体育社会学共同体有可能更好地评估体育在个人及其所形成的社区的生活中的作用和意义,它必须以有助于理论和概念的发展为出发点而构建知识体系,这些知识 跟所有人相关、为全人类服务,处理在地方、国家和全球等各个层面或大或小的问题,决定站在谁这一边,扮演一切神话的终结者,对权力、结构和控制进行批判性分析。悲哀的是,在不同文化中体育社会学人们某种程度上都陷入了同一种困境,他们被迫在职业和学科的竞 争中向他们在大学、国家和全球各各个层面的研究生们表明,他们学术发表的名声才是最重要的。摆脱这种局面并非易事。
考虑到体育社会学的未来,现在无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扩充它的理论基础(knowledge base)。地方和全球体育界正受到一系列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困扰,从某种程度上说体育也制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伦理问题加上治理和民主问题,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的断层伴随着环境问题。竞技体育表演也引发它对人类意味着什么这样意义深远的问题。这些是已经知道的和已经知道不知道的。还有大量体育社会学共同体尚未从内部或外部把握,可以说是不知道我们不知道的问题。
但也不用绝望。利用那些已经或即将退休的老人的知识,进一步与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及 人文学科的同事合作都会对研究有所帮助,为我们分支学科的持续存在提供一方安全的港湾。通过卓越科研中心培养未来的希望,欣赏同事而不是拆台,也会让事情朝着正确的方向 发展。探讨未来面临困境和挑战的主题会议也会为新生代学者的新思想提供论坛。
尽管现实中存在着重重障碍,体育社会学仍然必须证明它的重要性。就我个人而言,正如一开始所指出的,我当前和未来的课题是在全球体育的语境下探究身份、国家和民族主义。这就是我挥洒狂热的理智(passionate detachment)的地方。因此,我与阿尔斯特大学的凯 蒂·利斯顿博士共同研究爱尔兰、大英帝国和体育。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试图了解我们自己和他者的故事;同时,希望对主流社会学知识和体育社会学子学科有所贡献。在某种程度上,它可能有助于不列颠群岛人民之间更广泛的了解。这就是我们的未来所在。我们拭目以待。
本文刊于《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0年46卷第6期,转载引用请注明文章出处。

长按二维码关注
成都体育学院学报
编辑丨魏珂珂